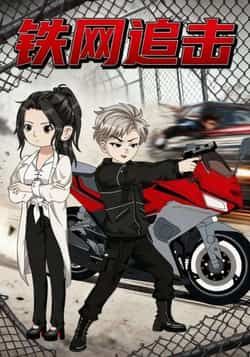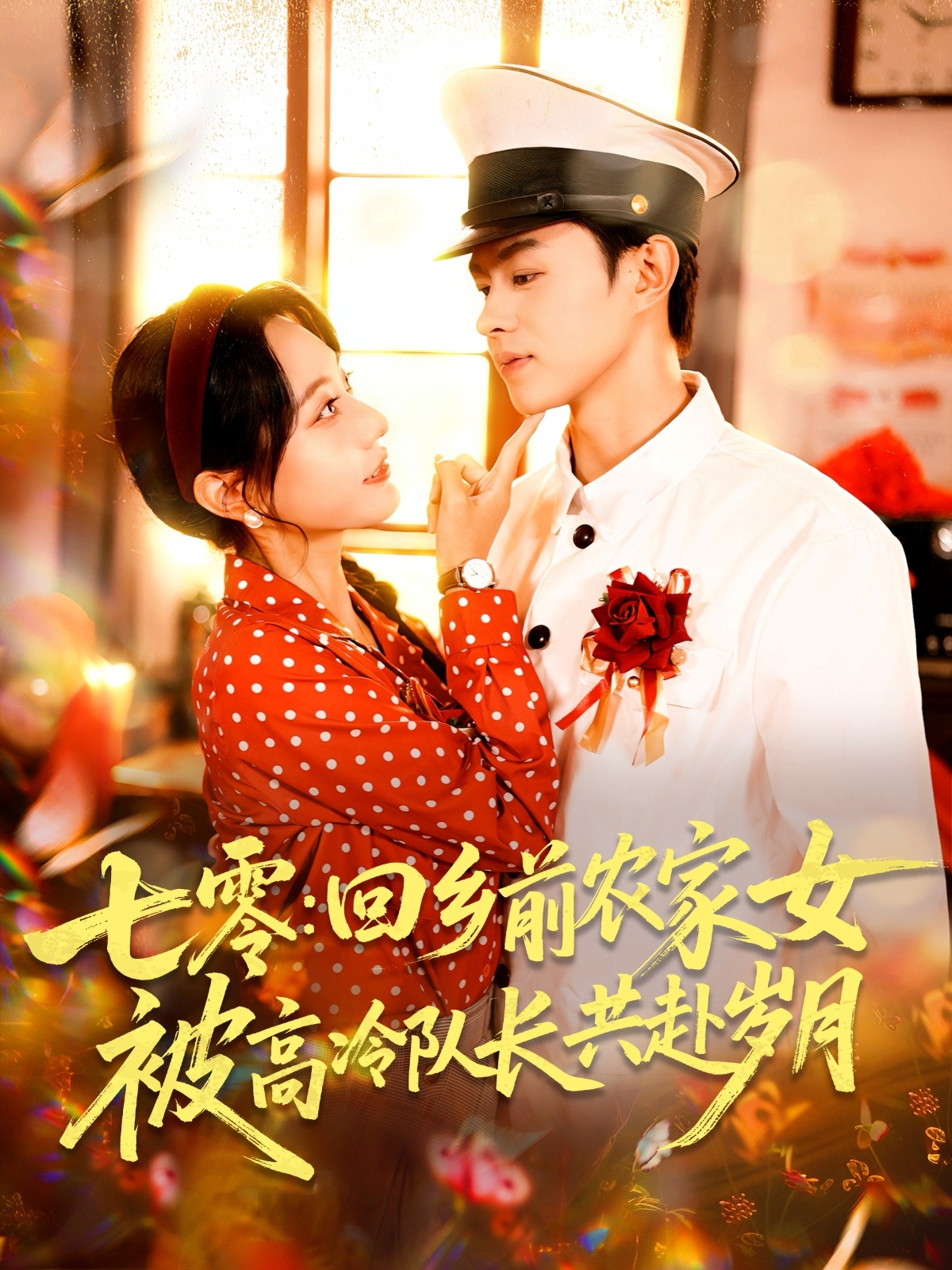
1977年的春风,吹皱了湘西山坳里的薄雾,也吹动了林秀行囊里那张皱巴巴的返乡证明,作为最后一批返城的知青,她在上海弄堂的欺凌与冷眼中熬了三年,最终揣着一身伤痕回到生养她的柳溪村,迎接她的,却不是记忆里炊烟袅袅的温暖——旱得裂口的田埂、村民躲闪的眼神,还有村口老槐树下,穿着蓝布褂子、眉头锁成川字的赵卫东。
这个比她大五岁的生产队长,是柳溪村说一不二的“铁面人”:说话像石头砸地,做事比犁铧还硬,上任三年,村里没一个敢在他面前耍滑,林秀刚到家,就因用城里带来的缝纫机给邻村姑娘做嫁衣,被扣上“投机倒把”的帽子,当着全村人的面,被他拎着站在晒谷场上。“林秀,知青的觉悟呢?”他声音不高,却像冰碴子扎进人心里,“想靠手艺发财?这根弦,从今天起给我绷紧了。”
倔强的林秀偏不信这根弦只能绷紧,夜里就着煤油灯翻出高中课本,把杂交稻的种植方法偷偷写在手帕上;白天,她带着村里妇女在田埂边试种,被赵卫东撞见,他瞪着眼骂“瞎胡闹”,转身却默默把自家分的半袋良种倒在她的试验田边,暴雨冲垮灌溉渠那夜,全村人心急如焚,林秀提出“竹笆引流法”,赵卫东哼了句“异想天开”,却扛起锄头第一个跳进泥水里,当清澈的水流重新淌进干裂的田地,他看着满身泥浆的林秀,喉头动了动,只闷闷说:“下回,先跟我商量。”
时代的浪潮终究裹挟着小村庄向前,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春风刮过柳溪村时,赵卫东顶着压力第一个在自家田里分地,却把最贫瘠的坡地留给了林秀,林秀攥着攒了半年的工钱买来菌种,带着姐妹们种木耳,赵卫东就带着男人们修山路,把一筐筐木耳背出山去,油灯下,他皱着眉算收成,她红着脸指出他算错的数;田埂上,他为她的“冒进”吹胡子瞪眼,却在她深夜生病时,默默把药放在她床头。
从青丝到白发,从柳溪村的晒谷场到更广阔的天地,他曾是她的“管教”,后来成了她的铠甲;她曾是他眼里的“刺头”,后来成了他的光,100集的岁月长卷里,铺开的是村庄从贫瘠到富庶的变迁,更是两个孤独灵魂在时代洪流中,用最质朴的方式书写的——始于严管、终于深情的泥土之歌。